2025-10-10
据工信部最新数据,2024 年我国大宗固废年产生量超 30 亿吨,累计堆存量突破 200 亿吨,占用耕地与林地超 100 万亩。过去 “填埋为主、利用为辅” 的处理模式,不仅造成资源浪费,还易引发土壤污染、地下水渗漏等问题。如今,随着 “双碳” 目标推进与技术创新,大宗固废处理已从 “被动减量化” 转向 “主动资源化”,形成协同处置、循环利用、高值化转化三大核心路径,逐步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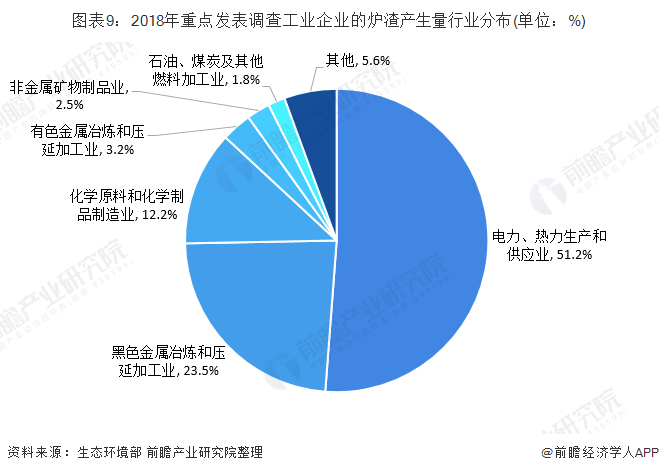
协同处置:传统手段的绿色升级
协同处置是对填埋、焚烧等传统技术的优化升级,通过将大宗固废融入现有工业生产体系,实现“以废代源”。其中,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最为成熟 —— 水泥生产过程中高温煅烧(1450℃以上)可彻底分解固废中的有害成分,同时固废中的无机成分能替代黏土、石灰石等原料,减少天然资源消耗。山东某水泥集团建成的协同处置线,每日可处理建筑垃圾、市政污泥等固废 800 吨,替代 30% 燃煤消耗,年减少碳排放约 5 万吨,产品质量仍符合国标要求。
电厂协同处置则聚焦煤矸石、粉煤灰等工业固废。山西某煤电企业将煤矸石破碎后与煤粉按1:4 比例混合燃烧,不仅解决煤矸石堆存问题,还因煤矸石含有的可燃成分降低燃煤成本,年消化煤矸石 50 万吨,节约标煤 3 万吨。这种 “以废补能” 模式,让传统电厂从固废产生源转变为处理端,形成闭环治理。
循环利用:构建规模化产业闭环
循环利用是大宗固废处理的主流方向,重点围绕建筑固废、尾矿、煤矸石等品类,打造“收集 — 破碎 — 再生 — 应用” 产业链。在建筑固废领域,深圳 2024 年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率达 85%,通过智能化分拣设备分离钢筋、混凝土、木材,其中混凝土破碎后制成的再生骨料,成功应用于深圳地铁 16 号线路基铺设,单项目节约天然砂石 20 万立方米,减少建筑垃圾填埋量 18 万吨。
尾矿的循环利用则突破“低端应用” 瓶颈。河北某铁矿将尾矿经磁选提纯、超细研磨后,制成轻质隔墙板,抗压强度达 3.5MPa,远超行业 2.5MPa 的标准,且导热系数低,兼具保温性能。该项目年产能 100 万立方米,可消化尾矿 150 万吨,产品覆盖京津冀地区市政工程,每吨尾矿的经济价值从 “负成本”(堆存费)提升至 200 元。
煤矸石的循环利用更形成“梯次开发” 模式:热值较高的煤矸石用于发电,发电产生的粉煤灰用于制砖,砖厂废料再用于路基填充。河南某矿区依托该模式建成循环经济园区,年处理煤矸石 200 万吨,衍生出电力、建材两大产业,带动周边 500 人就业,实现 “固废零堆存” 与区域经济增收的双赢。
高值化转化:挖掘固废潜在价值
高值化转化是近年来的创新突破,通过技术提取固废中的稀有成分或制备高附加值产品,让“废料” 变 “珍品”。粉煤灰的高值化利用最为典型,内蒙古某企业采用 “碱溶 — 沉淀 — 焙烧” 工艺,从粉煤灰中提取氧化铝,年处理粉煤灰 200 万吨,产出氧化铝 30 万吨,附加值较传统制砖提升 50 倍。同时,提取过程中产生的硅钙渣可进一步制成白炭黑,用于橡胶、涂料行业,实现 “吃干榨净”。
磷石膏的高值化转化则破解了磷化工行业的“环保痛点”。云南某磷化工企业将磷石膏与焦炭混合,在高温下分解生成硫酸和氧化钙,硫酸回用于磷矿加工,氧化钙制成水泥缓凝剂,年减少磷石膏堆存 80 万吨,同时创造产值 2 亿元。该技术打破了磷石膏 “只能填埋” 的局限,让磷化工产业从 “污染大户” 转向 “资源循环典范”。
电子废弃物虽不属于传统大宗固废,但随着产生量激增,也纳入高值化处理范畴。广东某企业研发的“物理分选 + 化学提纯” 技术,从废旧电路板中提取金、银、铜等贵金属,回收率达 99%,每吨废旧电路板可产出黄金 300 克、白银 2 千克,经济收益显著,同时避免了焚烧处理带来的二噁英污染。
挑战与未来趋势
当前大宗固废处理仍面临瓶颈:高值化转化的预处理成本较高,如粉煤灰提取稀有金属的预处理成本占总成本40% 以上;不同地区固废分类标准不统一,导致跨区域循环利用效率低下;部分技术如磷石膏分解需高温高压,能耗控制难度大。
未来,技术智能化与区域协同将成为突破方向。江苏某固废处理园区已引入物联网系统,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控固废运输、破碎、再生全流程,将处理效率提升20%,并降低 15% 能耗;“京津冀固废协同处置联盟” 则通过统一标准、共享设施,2024 年实现跨区域固废调配 150 万吨,避免 3 座小型填埋场建设。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与技术迭代,大宗固废处理将真正实现 “从环境负担到经济资源” 的价值重构,为工业绿色转型注入持久动力。